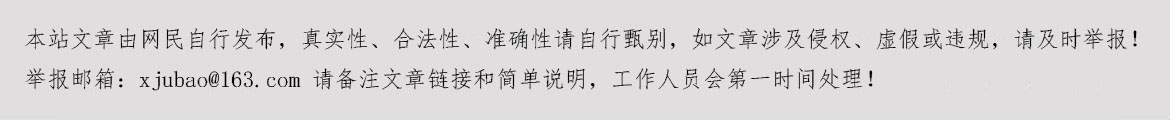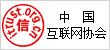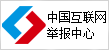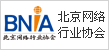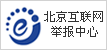张若梅:“双减”政策会缓解家长的焦虑吗?
2021-08-02 16:03:49
IPP评论是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
图源:网络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以下简称“双减”政策)。延续以往“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负担”的目标,这一次的“双减”政策对教培行业的乱象可谓重拳出击,而新成立的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则将以“钉钉子”的精神推动“双减靴子”的落地。
从政策目标而言,“双减”政策是对当下教培行业一次超强管制,是为“疯狂鸡娃”的家长们缓解教育焦虑和压力,将以往对教培行业的“运动式”治理转为常态化管理。但政策执行下的后续配套措施仍要对接学生及家长的实际需求,回应家长对孩子培优补差的关切,避免衍生新的教育痛点。
“双减”政策一规企业,二解民忧
第一,“双减”政策对现下野蛮生长、资本逐利的教培乱象做出回应。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拥有近百万家K-12校外培训机构,其中单机构营收规模超过10亿元的巨型校外培训机构约有25家,截至2019年市场规模已经超过8000亿元。资本的火热涌入让培训机构开始以做生意的方式来发展教育,个别机构甚至采用“白条”、“教育贷”等金融手段促销和吸引学员[1],当资金链断裂后企业则“一倒了之”,损害家长实际利益。
同时教培机构也存在贩卖焦虑、过度宣传、超前超标培训等违规情况,仅2020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有关教育培训服务的投诉就达到5.6万件,其中价格欺诈、虚假宣传、焦虑营销是主要乱象。
此次政策严格机构的准入制度、严禁资本化运作很大程度上是为过热的教培行业“降温”;同时建立培训内容备案和监督制度、严控学科类培训机构开班时间,则能有效遏制机构超前、超标培训,贩卖教育焦虑的情况。
第二,“双减”政策对起点抢跑、鸡娃成才的家庭焦虑做出回应。早在2018年《中国青年报》对2012名受访者进行的大范围调查中就显示,家长为孩子报培训班的目的在于“担心孩子落后、补习学业短板、防止孩子假期学习懈怠”。其中52.1%的家长坦言反感孩子上培训班,但在周围孩子都报班的情况下,只能被迫参与到补习的内卷游戏中。在义务教育的培训市场中,情况已经演化为:谁为教育投资的多谁便能获得更好的教育回报,教育的内卷已经让家庭承受了太多无效支出。
因此政策将教育责任重新回归学校,要求强化教师责任,提高学生作业质量,提供课后服务资源,并一针见血指出课后服务时间短、吸引力不强等问题,要求校方加大工作力度,以增强学生和家长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第三,“双减”政策将以往对校外培训行业的“运动式”治理变为常态化治理和高强度监管。据不完全统计,民办教育培训机构中的证照齐全比例不到20%,甚至相当比例的培训机构是在工商部门注册[2]。因此,监管过程中首先要回应的问题是:针对问题机构的治理究竟是教育部门,还是工商部门负责?
其次,培训机构的类别、培训内容、培训资质、退出机制缺乏具体要求。对此,今年年初教育部新设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以专门的监管机构来对教培机构进行常态化监管,避免教育部门和工商管理部门因行业资质问题产生“监管真空”;同时明确其监管职责,将机构准入、培训时间、人员资质、收费监管等都纳入管理范围。此次“双减”政策,更是要求建立培训内容备案与监督制度。亦即,明确监管部门、细化监管内容,国家消除教培行业乱象的决心,于此可见一斑。
治理不能只堵不疏,供需双方的痛点需要重视
第一,治理并非简单的“手起刀落”,后续配套措施仍要回应家庭的教育需求。教育培训的刚需客观存在,学科类的补差培优呼声仍在。在南都教育联盟调研报告中显示,如果取消周末或寒暑假培训班,63.51%的家长表示对辅导孩子学业有很大压力,61.69%比例的家长仍然希望在暑假为孩子报校外培训课程[3]。
因此落实“双减”政策仍需对接家长对校外培训机构的实际需求,如果仅仅关闭部分培训机构,禁止机构的学科教育培训,那么聘请私教,培训机构的“黑作坊”,将成为下一步政策治理的痛点所在。尤其是26.72%比例的家长称“将会聘请1对1家教”,如此减轻家庭教育负担的政策目标就难以达成。
如果将孩子的时间放回校内,那么如何让学生“吃饱”、“吃好”则是关键。按照政策要求,针对学科学习上的补差培优,校内将提供相应的学科辅导课程,但如此,将可能面临供给和需求两方的矛盾。因此治理校外培训机构只是一时之策,提供优质义务教育服务、回应家长的教育焦虑才是改革的根本。
第二,从供给方而言,如何让公立学校独立承担并提供家长满意的教育是治理之后的难点所在。这仅从基础教师数量低速增长、生师比等表征数据便可窥见一二。2010—2019年,我国基础教育教师数量(仅含小学及初中阶段专任教师)整体保持低速增长,甚至在2011—2015年专任教师增速不足1%。截至2019年专任教师数量为1001万人,同比仅上涨2.94%(详见图1)。
图12010—2019年中小学专任教师数量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教育部官网《教育统计数据》:http://www.moe.gov.cn/jyb_sjzl/
以2019年为例,我国小学阶段生师比为16.85:1,初中阶段生师比为12.88:1,未来若公立学校普遍开始延时托管服务,则势必在教师数量上捉襟见肘。此外区域间、校级间教育资源不均衡现象依旧突出,令家长满意的基础教育短期难以实现。以2018年城乡中小学专任教师学历层次为例,小学阶段的城区研究生学历专任教师是镇乡的3.2倍,初中阶段则为2.8倍。本科学历中,无论是小学阶段还是初中阶段,本科以上学历专任教师数量都远低于镇区及城区(详见表1)。
表12018年中小学阶段专任教师学历情况对比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9》
第三,从需求方而言,升学之路的淘汰率客观存在,家长如何心甘情愿将孩子教育完全交给学校?家长是否会将校外培训焦虑转嫁为对更好学校的追求,进而加剧学区房的热炒力度?当下尽管很多地区在硬件设施、生均经费以及教师配置方面逐年增加投入,也尝试用名校带领薄弱学校,以集团化办学和名师轮岗等手段来实现区域教育资源均衡化,但是家长头痛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升学率”,围绕升学率下的普职分流、高考分数的选拔机制,以及就业的“双非歧视”等问题加剧了家长对孩子教育的焦虑,这同样也是教培机构能够野蛮生长、学区房热度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在《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2018)》中,九成以上家长对子女成绩有一定要求,95%以上家长对子女成绩期望是“班级中等”,40%以上家长希望孩子成绩在“班级前三名”。即使学校教学水平相同,为了让孩子获得更高成绩和排名,家长也势必会额外投入更多教育资源,那么又谈何减轻学生负担、减轻家长负担呢?
解决供需双方痛点问题,需要多方合力
对于公立学校而言,自身既要补充现下不足的教师数量,借助集团化办学提升自身教学实力,同时也可借助规范性的培训机构作有益补充。其中培训机构的“学科类”项目,可联结中小学开展“进校服务”。一方面作为学校提供延时托管服务和暑期托管服务的力量补充。以专业学科培训教师来对当天课业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进行辅导和答疑,对学有余力的学生则组织他们开展文体活动、阅读、兴趣小组以及社团活动等。
另一方面为低线城市、乡村的薄弱学习提供教学革新、师资培训、管理优化等方面的服务。尤其近年来,部分头部教培机构的在线教育能够提供稳定的线上平台、优质线上课程资源等,这些“工具类”项目可以为校内精准化教学提供服务和产品。此外也可联结院校开展培训业务,创设“高校平台+机构资源”模式。例如联合师范类高校开展就业前培训,联结中小学开展教师及校长培训业务等。
对于家长而言,焦虑的不仅仅是当下的分数和择校,而是背后孩子的人生选择,且单凭政策制度也难以彻底解决此类焦虑。单就“普职分流”而言,现下1:1分流比例容易强化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心态,建议在鼓励职业教育的同时弱化对比例的强制要求。同时“双减”政策中的“健全作业管理机制、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的要求,具体执行标准和质量监控标准也有待地方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进行统筹规划,避免出现“一校一策”的情况。
参考文献:
[1]新华网.校外培训行业乱象频发,这是做教育,还是做生意[EB/OL].[2021-03-18].http://www.xinhuanet.com/2021-03/18/c_1127223962.htm.
[2]新华网.对症下药,规范民办教育培训机构[EB/OL].[2018-01-25].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8-01/25/c_1122312518.htm.
[3]澎湃新闻.校外培训的今天——双减在左,需求在右[EB/OL].[2021-07-15].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593070.
★本文作者:张若梅,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编辑:IPP传播
关于IPP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个独立、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由华南理工大学校友莫道明先生捐资创建。IPP围绕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政策、中国话语权与国际关系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国智库。
微信ID:IPP-REVIEW
国家高端智库
中国情怀国际视野
seo